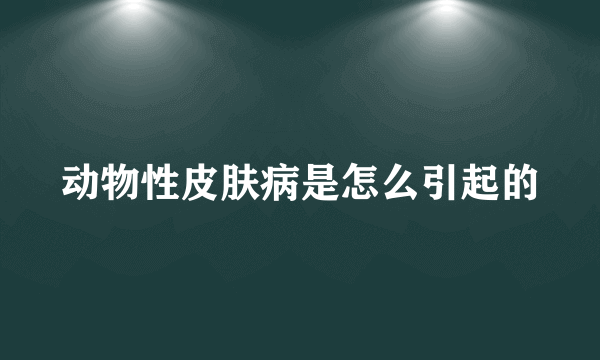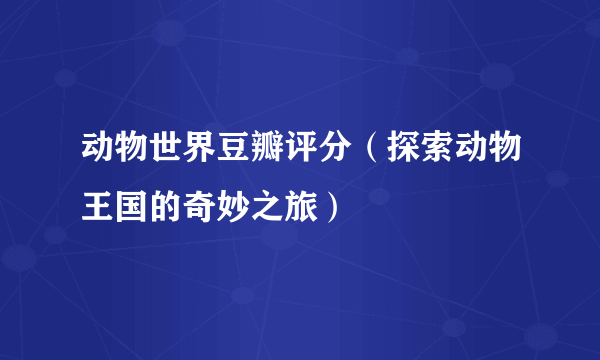两耳不闻窗外事,世上便无圣贤书
——读龙应台《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好几年前,记不得是几年,读到龙应台《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写作时间是1985年,1985年的大学生就不会“闹事”了?心里凉透。何况她写的是台湾大学生。果然都是中国人,大陆这边也以最快的速度、最麻利的动作学会了驯服。
最近在做一个“鲁迅主页”,想起这篇文章,又刊了出来。此时它真正打动我的倒是龙应台引用的《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记录了几个平凡而卑弱的“闹事者”,为抵制一部当红却涉及种族隔离的电影,一次次买票进影院再被人拖出去。捣乱的是年轻人,电影票对他们而言是奢侈的消费。当年,“种族隔离”虽然名声很臭,也不像现在这样被历史彻底抛弃掉,成了20世纪人类文明的一个污点。电影院的观众对这些“闹事者”,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大声喊“滚蛋!滚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
任何国家的民众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赞颂的历史往往就是他们现世反对的义行。做观众和做演员的感受根本不同,都愿意观看主角的流血和牺牲,却谁都不要出来真正受哪怕一点委屈,喝咖啡、读报纸的群众角色是现实世界最为推崇的,那些抢不到的倒霉蛋才干咽一口血骂着娘同主角闹事去了。万一成功,就也成了为后人羡慕的英雄,失败的话也不失为英雄主义的一员。成就的英雄是不谈英雄主义的,世人发明英雄主义,在于调和读史的伤心。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读到这里,我的全身也在颤抖。人是多么后知后觉、逆来顺受啊,噩运、暴行——统统以为可以混过去,甚至报应在自己身上也使劲忍耐着。“反抗”往往像挤牙膏一样被挤出来。人类在骨子里是多么迷恋和平、贪求安稳的动物。
龙应台对这段故事的论述远不如故事本身精彩。她提到了青年人的“道德勇气”,须以关心世界并独立判断为前提。在此我想:鲁迅先生等一批思想源泉性的人物,之所以反对徒手的请愿,一方面在于他们涉世极深,非常清楚: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是不肯动弹的,这“请愿”和“革命”相比,是太温和、太微弱的反抗。一方面他们也遗憾地看到:请愿者的队伍里,真正受“道德勇气”驱使的往往不多,他们固然关心这个世界,也极容易被世界收拾掉,对世界的恐吓和任何不友好的表示敏感惊忧。事实也是:破坏请愿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如周朴园拆解鲁大海领导的罢工,“你们的钱这次又灵了”,何止是“这次”,权势者要想认真反对请愿,请愿哪里是他们的对手。试问:马丁·路德·金若不是在民主国家,又碰上肯尼迪兄弟,被塞到黑牢去,割掉喉管、悄悄害死,哪里听他梦想的凯歌拨动了全人类的良知?至多是个有文化的鲁大海罢了。
“闹事”在今天仍应被“抽象继承”下来。固然看管理者、组织者怎么都顺眼,也不能从权利的武器库里取消“闹事”这条大枪。谁来闹事?队伍可以丰富起来,但青年人的作用抹杀不掉。自古中国人闹事就不以青年人为孤军。五四闹得成,还要感谢商界的响应。古久一点,“焚书坑儒”,不予合作的则纯粹一批老爷子。等到公车上书,闹事的就是一群中年人。“闹事”固然是最微弱的反抗,成果看也最不值得一提,背后的文明意义却很重大,它固然代表了一种道德勇气,也说明“我们是明辨是非的”,拒绝被骗,拒绝被蒙上眼奴役。闹事就像古代战场的军旗,插多少面军旗没实力还是要败,不插军旗也绝无可能凑成一场严肃的战局。
中国的历史教材里盛赞历朝历代的不安分者,尤其近代,任何形式、任何居心、任何效果的反抗都被肉麻地拎出来亮一亮,而今天的中国官方又是最怕人闹事的,层层渗透下去“顺民思维”。我们也终于被锻炼成电影院的观众,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滚!滚!滚!”,还有多少要“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正义言论的力量,换言之,道德勇气的力量——如果引起某个权力体的忌讳和深度敏锐的防范,不可能有好事等在后面。历史的说法:坑灰未冷,山东已乱;政治的说法:独裁的子宫已经成熟;文学一点的话,乔治·奥威尔:“想象一下一只靴子踩在脸上的感觉——那就是未来。”
什么事值得闹一闹?什么事非闹不可?
灭绝文化的事绝对值得闹一闹。试图打断你和这个世界的联系,也一定起来闹一闹。剩下的,我倒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闹的。比如政策不力,还要靠沟通和谈判去解决,我们也要理解中国官方一时难以消除的局限,不可能期望它支持一个马丁·路德·金出来。至于“抵制日货”,只可能成为流氓泛滥的借口。而“灭绝文化”和“隔绝世界”,是根本无从谈判的,它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压根儿没给你预备谈判桌。我总以为:有战略眼光的闹事不在于谋求一处谈判席,在于觉醒更多受蒙蔽的心灵。谈判席即便勉强给出,也不能以此为闹事的终点——当然,求全责备了。
谨慎地闹,还在于瞎闹、胡闹往往让高处的正义埋单受屈,真正要闹一闹的时候会发生“狼来了”的窘况。西方国家在去年遍地是示威游行,以致于法国人被戏称为“半年罢工,半年休假”,闹事变得太容易的话,其严肃性会相对削减。老谋深算的政府开放游行审批,让你随便闹、可劲闹,闹事者得到的同情反倒越来越少。前文说过:各国的国民本质上都一样,为的就是安稳的生活,坏政府也比没政府强,坏规则也比没规则强。
闹事背后还有一重意思,是专说给青年人的。即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世上便无圣贤书。社会的主体思潮是不支持青年人谈论国事,以天下为己任的,想法一露头,父母就过来说:“好好读书、好好工作,想那么多干啥?!”学校就过来一边劝一边威胁:“不要耽误自己的前程。”甚至要好的朋友也不和你站在一起,大伙离“闯祸胚子”都远远的。一方面,在于作为社会人,没有起码的安全感,随便是谁都能收拾你,还让你被收拾了也要写检查去确认侮辱。一方面,没人觉得“天下事”和“圣贤书”有必然的联系,甚至于,你一旦拿起圣贤书,就关闭了天下事的窗口。
圣贤书当然要和天下事紧密地列在一起。圣贤都是死人了,指望这些枯骨去指教你如何思想、如何实践是难为人家。圣贤也都是后人捧起来的,鲁迅先生就一再说过:中国人消灭人要么是搞掉,要么是捧起来。这些被捧起来的圣贤固然伟大,我们也往往在仰角处忘了平视真实。再有,圣贤所以能流传,还在于他们确实说的有道理,但究竟有道理在哪里?需要我们一手捧着书一手推门进入社会。道理不是讲出来的,是试出来的。讲道理的圣贤总要倒掉,还有多少人记得二程朱熹都说过什么?但孔子的一些话却是中国人的共同默契。为什么呢?在中国人轰轰烈烈的人格实验中,孔子的教训是好使的,孔子之徒真君子多,朱子之徒伪君子多。
很能理解今天的中国人对闹事的反感,尤其年轻人对闹事的抵触。好不容易过了几年好日子,哪有那么多意见?!确实,今天的中国,值得闹一闹的事不多,毁坏文明或者隔绝世界都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只作为个别事故出现,可以赦免。但“闹事”也起码是个“中性词”而不至于沦为纯粹的贬义词。况且要读圣贤书,关心国事总是不错的。历史上看:文明只不过是瘸着前进,社会并不必然越来越好,具体到区域,情况更复杂。今天依然有奴隶制度,依然有人吃人的血案,依然有灭绝文化、隔绝世界的暴行。为防止世道沦丧之时要付出额外惨痛的代价,最好不要只读闹事的历史,而忘了现实也可以反抗,也可以合理斗争。
过几年再抽出这篇文章,应该不会颤抖了吧。“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一方面要发现社会,更要紧的是发现人,发现人的价值,也认识到人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