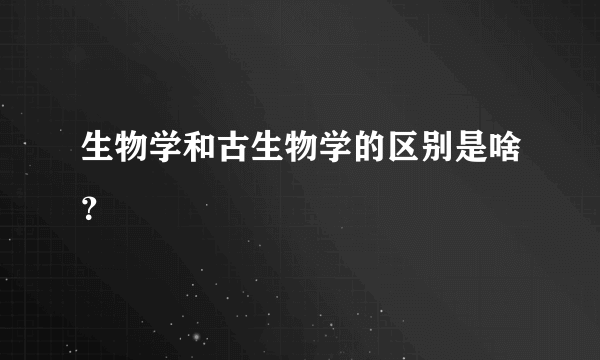NassirGhaemi,MD,MPH,美国塔夫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塔夫斯医学中心心境障碍项目主任每当我对ADHD及边缘性人格障碍之类疾病的诊断效度表示质疑时,我经常会受到这样的诘问:“它们确实造成了大脑的X改变、Y改变、Z改变……不信可以看大脑影像学的片子,这怎么能忽略呢?难道这些改变还不能证明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生物学疾病吗?”如果你承认,通过阅读NassirGhaemi也就是我在Medscape上发布的文章,你受到了我施加给你的影响,从而患上了“Medscape病”,那么上述说法或许可以成立。假如现在就有一台可以进行放射配基结合分析的功能磁共振机,当你阅读这篇文章时,它完全可以显示出你脑血流的变化,甚至多巴胺系统的活性。我们对于精神科概念的理解不够透彻,因而混淆了“生物学因素”和“疾病”这两个术语。并非所有生物学的东西都是疾病,即使我们可以将疾病定义为具有生物性因素。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类所有的心理体验均由大脑所介导,而每个人只有一个大脑,因此当我们心中暗潮涌动时,大脑总会有一些生物性变化。阅读有关大脑的文章也是一种心理过程,精神分裂症患者产生妄想也是一种心理体验。
第一种大脑改变显然不能反映某种疾病,
第二种才可以。因此,展示成人ADHD及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的大脑磁共振图像变化,与证明这些状况是疾病,两者并无直接关系。如果你疯狂地看电视或玩游戏,你的大脑会发生改变,你也可能出现ADHD的临床症状;如果你不止一次被性虐待,你的大脑会发生改变,你也可能出现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临床症状。然而,与21-三体综合征、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等存在彻头彻尾的遗传基础的疾病相比,ADHD及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大脑所发生的变化并非扮演相同的病因角色。在“真正”的疾病个案中,生物学变化总是病因性的:它们导致了临床症状的出现;在边缘性人格障碍或注意缺陷个案中,生物学变化是临床症状的效应,而非病因。生物学因素不等同于疾病,因为它常常反映发病机制,而非病因。大脑是所有心理体验共同的最终通路,但大脑的变化不是上述心理体验的最终原因,它们始终是近因,而不是终极原因。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不寻常:很多精神科医生比心内科医生还重视所谓的“生物学因素”。我们精神科医生总是在强调ADHD的生物学原因,这样在开具苯丙胺处方时,我们心里能好受一些,尽管这类药物对神经系统实际是有害的;我们精神科医生希望强调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生物学因素,这样在开具诊断证明书时,我们心里能好受一些,而且可以不用诊断双相障碍,也不用开心境稳定剂。在我们的思想体系中,我们把“生物学因素”当成某种立足点。甚至连心理分析这一长期反生物学思维的堡垒也华丽变身为“神经心理分析”(neuropsychoanalysis),从而为自己正名。既然大脑是共同的最终通路,那么所有东西都可谓具有生物学因素,也包括这篇文章,而它也并不能代表哪里有什么东西病了。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必须将生物学因素的范围从发病机制中延伸出来,毕竟与具有诊断意义的病因相比,发病机制是琐碎而不值一提的。事实上,这一过程已经出现在许多针对精神分裂症及双相障碍的确切的遗传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心理及社会因素才是边缘型人格障碍以及PTSD、分离转换障碍的病因,而成人ADHD的病因学证据效力目前仍很微弱。请不要引用某些为成人ADHD遗传学病因摇旗呐喊的文献,这些研究完全没有校正ADHD可能共病的其他临床状况,包括双相障碍。我在其他地方看到过这些研究,它们的结果均不成立。所以说,除非我们愿意区分病因和发病机制,不然还是暂且把“生物学因素”束之高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