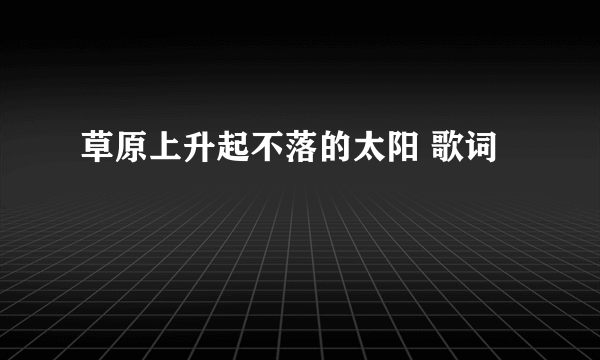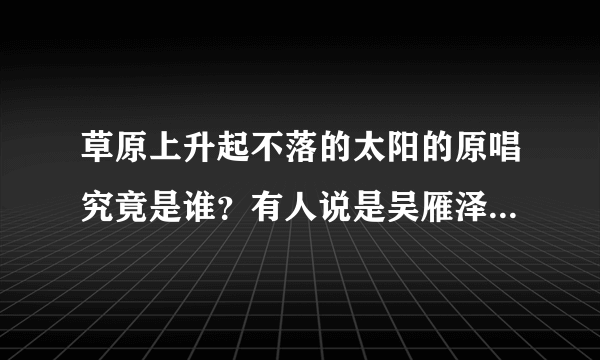《草原》的体裁是散文。《草原》是老舍于1961年创作的一篇散文。这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抒情散文,作者用清新的笔触记叙了自己到内蒙古草原访问时所看到的美丽景色和蒙古族同胞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汉族同胞的动人情景。文章思路严谨,结构精妙,主旨鲜明,文字优美,意蕴隽永,赞美了祖国山河的壮丽,歌颂了民族团结的情谊。
草原
自幼就见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类的词句。这曾经发生过不太好的影响,使人怕到北边去。这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天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都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的。羊群一会儿上了小丘,一会儿又下来,走在哪里都像给无边的绿毯绣上了白色的大花。那些小丘的线条是那么柔美,就像没骨画那样,只用绿色渲染,没有用笔勾勒,于是,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
这种境界,既使人惊叹,又叫人舒服,既愿久立四望,又想坐下低吟一首绮丽的小诗。在这境界里,连骏马与大牛都有时候静立不动,好像回味着草原的无限乐趣。紫塞,紫塞,谁说的?这是个翡翠的世界。连江南也未必有这样的景色啊!
我们访问的是陈巴尔虎旗的牧业公社。汽车走了一百五十华里才到达目的地。一百五十里全是草原。再走一百五十里,也还是草原。草原上行车至为洒脱,只要方向不错,怎么走都可以。初入草原,听不见一点声音,也看不见什么东西,除了一些忽飞忽落的小鸟。
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了迂回的,明如玻璃的一条带子。河!牛羊多起来,也看到了马群,隐隐有鞭子的轻响。快了,快到公社了。忽然,像被一阵风吹来的,远丘上出现了一群马,马上的男女老少穿着各色的衣裳,马疾驰,襟飘带舞,像一条彩虹向我们飞过来。
这是主人来到几十里外,欢迎远客。见到我们,主人们立刻拨转马头,欢呼着,飞驰着,在汽车左右与前面引路。静寂的草原,热闹起来:欢呼声,车声,马蹄声,响成一片。车、马飞过了小丘,看见了几座蒙古包。
蒙古包外,许多匹马,许多辆车。人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外乘马或坐车来看我们的。我们约请了海拉尔的一位女舞蹈员给我们作翻译。她的名字漂亮——水晶花。她就是陈旗的人,鄂温克族。主人们下了马,我们下了车。
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总是热呼呼地握着,握住不放。我们用不着水晶花同志给作翻译了。大家的语言不同,心可是一样。握手再握手,笑了再笑。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总的意思都是民族团结互助!
也不知怎的,就进了蒙古包。奶茶倒上了,奶豆腐摆上,主客都盘腿坐下,谁都有礼貌,谁都又那么亲热,一点不拘束。不大会儿,好客的主人端进来大盘子的手抓羊肉和奶酒。公社的干部向我们敬酒,七十岁的老翁向我们敬酒。正是:
祝福频频难尽意,举杯切切莫相忘!
我们回敬,主人再举杯,我们再回敬。这时候鄂温克姑娘们,戴着尖尖的帽儿,既大方,又稍有点羞涩,来给客人们唱民歌。我们同行的歌手也赶紧唱起来,歌声似乎比什么语言都更响亮,都更感人,不管唱的是什么,听者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饭后,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姑娘们表演了民族舞蹈。客人们也舞的舞,唱的唱,并且要骑一骑蒙古马。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是呀!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
人的生活变了,草原上的一切都也随着变。
看那马群吧,既有短小精悍的蒙古马,也有高大的新种三河马。这种大马真体面,一看就令人想起“龙马精神”这类的话儿,并且想骑上它,驰骋万里。牛也改了种,有的重达千斤,乳房像小缸。牛肥草香乳如泉啊,并非浮夸。羊群里既有原来的大尾羊,也添了新种的短尾细毛羊,前者肉美,后者毛好。是的,人畜两旺,就是草原上的新气象之一。
这篇文章出自老舍的游记《内蒙风光》,全文收在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的《小花朵集》。1961年夏,老舍与一批作家、画家、音乐家、舞蹈家、歌唱家等二十来人,应乌兰夫邀请,由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文联组织,到内蒙古东部、西部参观访问八周,看了林区、牧区、农区、渔场、风景区、工业基地和一些古迹、学校、展览馆。游记分七节对上述内容依次作了介绍,牧区的一节小标题为《草原》,即这篇文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牧区在作者面前展现了一幅美丽的草原景色和一派人畜两旺的气象,蒙古族同志对作者一行的热情款待又充分体现了民族团结亲如兄弟的一幕幕动人景象。这一切,都大大激发了作者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团结事业的热爱之情,使他难以抑制地要抒发出来。
然而,作者的感情又十分深挚与含蓄,因此,他没有用直抒胸臆的笔法来畅怀讴歌,而是采取了间接抒情的手法,让激情在写景、叙事、状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从而使文章充满了感情色彩,显得分外真切感人。
首先是作者对草原景色的描绘。画笔是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天空是青苍蔚蓝的颜色,草原无边无际,一片茫茫。风儿吹过,牧草低伏,显露出原来隐没于草丛中的众多牛羊)”勾起的。
北朝民歌《敕勒歌》中的这三句诗饱含了当时人们低沉的感慨,浸透了悲怆的幽情。然而时代变了,“天”不再“苍苍”了,它“明朗”“清新”得令人总想愉快地“高歌一曲”;“野”也不再“茫茫”了,“翠色欲流”的草原令人“舒服”得直想“低吟”小诗;“牛羊”也无须“风吹草低”时才显现了,连“骏马和大牛”都好像在回味着“无限乐趣”。
依着三句诗的顺序,作者明快地作了令人信服的对比,绮丽的色彩把旧时代的感慨与幽情一扫而空,对草原景色的赞美之情借托着“紫塞,紫塞,谁说的?”这样的反问句,由衷地吐露了出来。昔“紫”今“翠”,基调上的鲜明对比,甚至使作者感慨道:“连江南也未必有这样的景色啊!”这里,寓情于景,情由景生,无须多用抒情笔墨,浓烈的情绪就从令人赏心悦目的草原画面中溢出来了。
接着是作者对牧业公社的访问的记叙。记叙是以时间为顺序的。迎客、交谈、款待、尽欢,这一个又一个场面并未着意铺排,也绝少浓笔涂抹,读来仍不失明丽浓烈之感。关键依然在感情的抒发上。如果说,写景时是寓情于景,情由景生,那么,叙事时就是融情于叙,情由事托了。
譬如,写迎客。花那么多笔墨写初入草原时的静寂和空旷,无非是借此衬托好客的主人迎出几十里外的那幅有声有色的热闹画面。画面中融注的正是蒙汉兄弟之间的深情厚谊。
再如,写交谈。不写交谈的内容,不介绍几句精彩的对话,而偏偏要写那位翻译“水晶花”,这是为了强调交谈是在言语不通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此时此地,这位必不可少的人物却恰恰“用不着”了。因为尽管“你说你的(蒙语)”,“我说我的(汉语)”,“总的意思”却是心心相印,“都是民族团结”。这是亲密无间的手足之情的又一次别有风味的抒发。
又如,写款待。写主客“谁都有礼貌,谁都又那么亲热,一点不拘束”。“有礼貌”却又“不拘束”,看似有点矛盾,实则这两个侧面实在是统一的。而且还是统一在“情”上。因为有情,主客就互相尊敬,皆有礼貌,因为有情;不讲虚伪客套,就能毫不拘束。洋溢在这场面中的还是一个“情”字。
这类融情于叙的语句比比皆是。诸如,用独词句“河!”所表达的猛然见到河水的欣喜之情;“也不知道是谁的手,总是热乎乎地握着,握住不放”所体现的不分彼此的友爱之情;“也不知怎的,就进了蒙古包”所流露的生活在友谊海洋之中的微醉之情;“太阳已经偏西,谁也不肯走”所暗示的流连忘返之情,都使这次访问带上了浓烈的感情色彩。
至于相继出现的“祝福频频难尽意,举杯切切莫相忘”和“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夕阳”这两组诗句当然更是把感情凝聚起来的点睛之笔。
最后是作者对草原上牲畜的描绘。描绘的笔集中在马、牛、羊三种牲畜上。对马的介绍,主要通过感受,“真体面”,“令人想起龙马精神”,“想骑上它”,字里行间,包含着赞赏之情;对牛的介绍,主要借助描绘,“重达千斤”“乳房像小缸”的形象,化成诗句“牛肥草香乳如泉”,惊叹之情溢于言表;对羊的介绍,则主要进行评价,“肉美”,“毛好”,流露出的依然是喜不自禁的夸耀之情。和“寓情于景”、“融情于叙”相匹配,这里的状物可以称得上“借情赏物,情随物移”了。
总之,无论是草原景色的描绘,访问过程的记叙,还是牲畜情况的介绍,“桩桩件件总关情”,处处饱含着作者强烈而又含蓄、鲜明而又深挚的感情。这或许就是一千多字的文章却能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之所在。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现代小说家、戏剧家、人民艺术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一生创作极勤,硕果累累,主要作品有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茶馆》,儿童剧《宝船》等,其作品多选材于自己所熟悉的城市下层居民生活,通过塑造极为生动的人物形象、于“平常”中透出深刻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