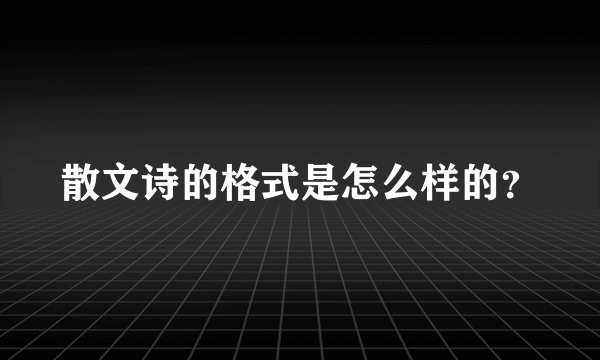简桢之<四月裂帛>
三月的天书都印错,竟无人知晓。
近郊山头染了雪迹,山腰的杜鹃与瘦樱仍然一派天真地等春。三月本来无庸置疑,只有我关心瑞雪与花季的争辩,就像关心生活的水潦能否允许生命的焚烧。但,人活得疲了,转烛于缁铢、或酒色、或一条百年老河能不能养得起一只螃蟹?于是,我也放胆地让自己疲着,圆滑地在言语厮杀的会议之后,用寒鸦的音色赞美:“这世界多么有希望啊!”然后,走。
直到一本陌生的诗集飘至眼前,印了一年仍然初版的冷诗,(我们是诗的后裔!)诗的序写于两年以前,若洄溯行文走句,该有四年,若还原诗意至初孕的人生,或则六年、八年。于是,我做了生平第一件快事,将三家书店摆饰的集子买尽——原谅我鲁莽啊!陌生的诗人,所有不被珍爱的人生都应该高傲地绝版!
然而,当我把所有的集子同时翻到最后一页题曰最后一首情诗时,午后的雨丝正巧从帘缝蹑足而来。三月的团云倾倒的是二月的水谷,正如薄薄的诗舟盛载着积年的乱麻。于是,我轻轻地笑起来,文学,真是永不疲倦的流刑地啊!那些黥面的人,不必起解就自行前来招供、画押,因为,唯有此地允许罪愆者徐徐地申诉而后自行判刑,唯有此地,宁愿放纵而不愿错杀。
原谅我把冷寂的清官朝服剪成合身的寻日布衣,把你的一品丝绣裁成放心事的暗袋,你娴熟地三行连韵与商籁体,到我手上变为缝缝补补的百衲图。安静些,三月的鬼雨,我要翻箱倒箧,再裂一条无汗则拭泪的巾帕。
我不断漂泊,
因为我害怕一颗被囚禁的心,终于,我来到这一带长年积雨的森林
你把七年来我写给你的心还我,再也没有比这更轻易的事了。
约在医院门口见面,并且好好地晚餐。你的衣角仍飘荡着辛涩的药味,这应是最无菌的一次约会。可惜的,惨淡夜色让你看起来苍白,仿佛生与死的演绎仍鞭笞着你瘦而长的身躯。最高的纪录是,一个星期见十三名儿童死去,你常说你已学会在面对病人死亡之时,让脑子一片空白,继续做一个饱餐、更浴、睡眠的无所谓的人。在早期,你所写的那首《白鹭鸶》诗里,曾雄壮的要求天地给你这一袭白衣;白衣红里,你在数年之后《关渡手稿》这样写:
恐怕
我是你的尸体衣裳
非婚礼华服
并且悄悄地后记着:“每次当病人危急时,我们明知无用,仍勉强做些急救的工作。其目的并非要救病人,而是来安慰家属。”
你早已不写诗了,断腕只是为了编织更多美丽的谎言喂哺垂死病人绝望的眼神。也好让自己无时无刻沉浸于谎言的绚丽之中,悄然忘记四面楚歌的现实,你更瘦些,更高些,给我的信愈来愈短,我何尝看不出在急诊室、癌症病房的行程背后,你颤抖而不肯落墨讨论的,关于生命这一条理则。
终于,我们也来到了这一刻,相见不是为了圆谎为了还清面目,七年了,我们各自以不同的手法编织自己的谎,的确也毫发未损地避过现实的险滩。唯独此刻,你愿意在我面前诚实,正如我唯一不愿对你假面。那么,我们何其不幸,不能被无所谓的美梦收留,又何等幸运,历劫之后,单刀赴会。
穿过新公园,魅魅魉魉都在黑森林里游荡,一定有人殷勤寻找“仲夏夜之梦”,有人临池摹仿无弦钓。我们安静地各走各的,好象相约要去探两个挚友的病,一个是七年前的你,一个是七年前的我。好象他们正在加护病房苟延残喘,死而不肯瞑目,等亲人去认尸。
“为什么走那么快?”你喊着。
“冷啊!而且快下雨了。”
灯光飘浮着,钢琴曲听来像粗心的人踢倒一桶玻璃珠。餐前酒被洁净的白手侍者端来,耶稣的最后晚餐是从哪儿开始吃的?
“拿来吧,你要送我的东西。”
你腼腆着,以迟疑的手势将一包厚重的东西交给我。
“可以现在拆吗?”我狡诈地问。
“不行,你回去再看,现在不行。”
“是什么?书吗?是圣经?……还是……真重哩!”我掂了又掂,七年的重量。
“你……回去看,唯一、唯一的要求。”
于是,我装做什么都不知道,继续与你晚餐,我痛恨自己的灵敏,正如厌烦自己总能在针毡之上微笑应对。而我又不忍心拂袖,多么珍贵这一席晚宴。再给你留最后一次余地,你放心,凄风苦雨让我挡着,你慢慢说。最后一封信这样落笔:“在我心目中,你一直是个尊贵的灵魂,为我所景仰。认识你愈久,愈觉得你是我人生行路一处清喜的水泽。
“为了你,我吃过不少苦,这些都不提。我太清楚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困难,遂不敢有所等待,几次想忘于世,总在山穷水尽处又悄然相见,算来即是一种不舍。
“我知道,我是无法成为你的伴侣,与你同行。在我们眼所能见耳所能听的这个世界,上帝不会将我的置于你的手中。这些,我都已经答应过了。
“这么多年,我很幸运成为你最大的分享者,每一次见面,你从不吝啬把你内心丰溢的生息倾注于我的杯。像约书亚等人从以实各谷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有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你让我不致变成一个盲从的所知障者,你激励我追求无上自由的意志,如果有一天我终能找到我的迦南之野,我得感谢你给我翅膀。
“请相信,我尊敬你的选择,你也要心领神会,我的固执不是因为对你的任何一桩现实的责难,而是对自己个我生命忠贞不二的守信。你甚美丽,你一向甚我美丽。
“你也写过诗的,你一定了解创作的磨坊一路孤绝与贫瘠,没有一日,我卑微的灵不在这里工作、学习。若我有任何贪恋安逸,则将被遗弃。走惯贫沙,啃过粗粮,吞咽之时竟也有蜜汁之感,或许,这是我的迦南地。
“不幻想未来了。你若遇着可喜的姊妹,我当祈福祝祷。你真是一个令人欢喜的人,你的杯不应该为我而空。
“就这样告别好了,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
且让我们以一夜的苦茗
诉说半生的沧桑
我们都是执著无悔的一群
以飘零作归宿
在你年轻而微弱的生命时辰里,我记载这一卷佶屈聱牙的经文,希望有朝一日,你为我讲解。
如果笔端的回忆能够一丝丝一缕缕再绕个手,我都已经计算好了,当我们学着年轻的比丘比丘尼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食,还至本处时,我要把钵中最大最美的事物供养你,再不准你像以前软硬兼施趁人不备地把一片冰心掷入我的壶。
我们真的因为寻常饮水而认识。
那应该是个薄夏的午后,我仍记得短短的袖口沾了些风的纤维。在课与课交接的空口,去文学院天井边的茶水房倒杯麦茶,倚在砖砌的拱门觑风景。一行樱瘦,绿扑扑的,倒使我怀念冬樱冻唇的美,虽然那美带着凄清,而我宁愿选择绝世凄艳,更甚于平铺直叙的雍容。门墙边,老树浓荫,曳着天风;草色釉青,三三两两的粉蝶梭游。我轻轻叹了气,感觉有一个不止名的世界在我眼前幻生幻化,时而是一段佚诗,时而变成幽幽的浮烟,时而是一声惋惜——来自于一个人以生中最精致的神思……这些交错纷叠的灵羽最后被凌空而来的一声鸟啼啄破,然后另一个声音这么问:
“你,就是简媜吗?”
我紧张起来,你知道的,我常忘记自己的名字,并且抗拒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那一天我一定很无措吧!迟疑了很久才说:“是。”又以极笨拙的对话问:“那,你是什么人?”
知道你也学中文的,又写诗,好像在遍野的三瓣酢浆中找到四瓣的幸运草:“唷,还有一棵躲在这!”我愉快起来就会吃人:“原来是学弟,快叫学姊!”你面有难色,才吐露从理学院辗转到文学殿堂的行程,倒长我二岁有余。我看温文又亲和,分明是邻家兄弟,存心欺负你到底:“我是论辈不论岁的!”你露齿而笑,大大地包容了我这目中无人的草莽性情。那一午后我归来,莫名地,有一种被生命紧紧拥住的半疼半喜,我想,那道拱门一定藏有一座世界的回忆。
毕竟,我只善于口头称霸,在往后与你书信嬗递,才发觉你瘦弱的身躯底下,凝练了多少雄奇悲壮的天质,而你深深懂得韬光养晦,只肯凿一小小的孔,让琢磨过的生命以童子是姿势嬉嬉然到我眼前来。我们不谈身世只论性命,更多时候在校园道相遇,也只是一语一笑作别,但我坚信:“这人是个大寂寞过的人!”
那时侯,你的面目早已因潜伏的病灶难靖,稍稍地倾斜着,反正已经割过了而且是个慢性子的瘤,就不必管吧,只在你心力交瘁的时候,才憔悴起来,我叫你当心,你复来的信不痛不痒地说:“今早文心课见你挽抱书飘然而去,霎时间萌生一种远飏的感觉,没来得及跟你说。有回上声韵,下了课,正见你倦极而伏案,其时感觉也是一惊。记得有次夜深,与你不期而遇,你说从总图出来,回宿舍去。夜色下的你步履决定,却透着层弱倦后的苍白。一直没能多问候你,反而是你看出我的憔悴。”你始终不愿意称我“简媜”,说这二字太坚奇铿
我该找这个世界谈谈 文-吴会得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 . 这并非是我逃避的原因 . 我依旧有很多憧憬,对梦想,对记忆,对失败,对希冀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 >................. 题记 自 从伊伊学舌, 蹒跚 学步到明事理 , 我们携带着与生俱来的天真一点一点的熟悉这个世界。或许是太过于诗意,天公不作美,总是有如雕塑般的一刀一刀残酷的斩杀着那与生俱来的东西。可是我们又该拿什么去熟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又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概念,然而所有的概念都是脆弱的。可是我们却总是难以把握这个世界的宽度与尺度,于是,随着我们逐渐长大,现实变得如此般残酷,理想,记忆,失败,希冀纵横交错,让我们眼花缭乱又束手无策,不得不承认我和这个世界不熟,以致,我想找这个世界谈谈。 有一个孤单的孩子,他有单薄的身子骨儿,薄薄的嘴唇,薄薄的舌头,薄薄的眼皮儿,甚至是薄薄的指甲,因此,他有了个美丽可爱的名字—— 纸片人。
纸片人不喜欢白天,白日里阳光射下的一束束刺眼的光线,他觉得足可以穿透自己的五脏六腑,他便惶恐不已,生怕自己那点小秘密会从口袋里蹦出来。对于白天五彩斑斓,花红酒绿的世界来说,他仿佛只是空气而已,飘飘荡荡,恍恍惚惚。然而,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行走在周围的四肢发达的人们,怎么可以伪装得如此滴水不漏。明明心里看彼此不顺眼,却能够面上含笑,称兄道弟,明明长得很委婉,行为很畏琐,却可以被恭维她的人描绘成面容姣好,宛若桃花,品性善良,尤如菩萨。因而,纸片人常常会想一个问题:桃花和菩萨的综合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他看不懂生活在这个白天世界里的一切生灵,总觉得这些生灵的灵魂并不是与生俱来,是这样的白天世界创造了这样陌生的灵魂。
纸片人才不想被这样的灵魂操纵自己单薄的身体呢?故而,他喜欢行走在静寂的夜空下,形单影只,但很快乐。一盏又一盏明亮的街灯将他孤单的身影拉长又缩短,缩短又然后又拉长。这样反反复复,乐此不疲。他竟还张开双臂,双脚微微弯曲一用力,就可以轻飘飘地飞起来了。没有刺眼的阳光,没有令人反感的各怀鬼胎和心照不宣,没有飞驰而过的汽车的呼啸,只有这安详静谧的苍穹,还有夜空里挂着的无数耀眼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尤如一位快乐的钢琴家手指缝里流出的一串串动人的音符,纸片人怕是被这迷人的夜弄醉了,还真以为这些美丽的音符是自己薄薄的脚趾头踩出来的呢?
就这样一直在夜空下行走着,快乐地走着,纸片人并不担心,如果没有了街灯,他会提着那令他骄傲的红灯笼,快乐地去寻找那令人骄傲的未来。是的,有一天,他会令疼爱他的爸爸妈妈骄傲,令关心爱护他的好朋友们骄傲。设若有一天走累了,就停下来,把自己单薄的躯体和丰满的理想融入这片曾与他相依为命的夜空里,这样,他会觉得这片夜是属于他的了,他依然可以生活在夜的世界里。 单薄的纸片人,快乐的纸片人,勇敢地行走在夜空下。 其实他就是我现实生活的写照,我想我该找这个世界谈谈。 冬天来了,身体变得极度畏冷,越冬也就成了一件极为难堪的事,大学的宿舍里很冷,没有火炉,没有暖气。我穿保暖衣,盖两床被子,可是还是睡不到天明。 又在四点钟的时候醒来。我搓着双手,点上一只烟在窗前,冬天的早晨像一个呆傻的老人,空气里充斥着从他身上脱落下来的皮屑,呼入口中,立即被陈年的悲凉哽住了。但是这种哀老,朽坏的气息我是不怕的。反倒是亲切,它让我想起我外婆来. 外婆是我童年里唯一有轮毂的角色. 母亲生性外向活泼 , 总是忙着工作 , 好几天见她一面也是很寻常 . 父亲一直在外地 , 过年的时候才回家 , 于是年幼的我总是在他陌生的站在我面前时不免很吃惊 . 只有外婆她总是在, 甚至几个月不出门 . 可是她在我六岁时犯精神病 , 在疯癫中度过 . 每天除了谁七哥小时外 , 其它时间都在自言自语 , 神经紧张 , 总觉得有人要加害与她 . 意志偶尔也会格外清晰 , 于是死活不让我出去玩耍 , 总担心有人加害于我 . 我到七岁时才入学 , 此前没有任何玩伴 . 十岁大的时候, 父亲下岗了 , 回到了家里 . 原来他是个内心虚弱的赌徒 . 对母亲很依赖 , 常问她要钱 , 又不让她出门 . 发生争执时他总会大打出手 , 外婆很害怕 , 她抱着我躲在衣柜里 . 但是她却很快忘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 蜷缩在黑暗里 , 自言自语起来 . 三年后 , 母亲和父亲离婚了 , 父亲搬走了 . 此后 , 母亲总是和邻居在门口吵架 . 有时在大喊大骂的讲电话 . 外婆就拉着我往衣柜里躲 ,. 那时我已经懂事了 , 挣开了她的手 , 她没有失望 , 她自己去了 . 不久外公去世了, 母亲瞒了好几个月才让外婆知道 . 母亲说着说着痛哭了起来 . 外婆见不得有人哭 , 她错愕的站起来 . 躲进了衣柜里 . 现在想来, 她也许不是真的害怕 , 她只是不想看见不想听见罢了 . 不想让身外的一切妨碍到她 . 母亲常说这种疯癫是有遗传性的 , 每一代好像必须有一个人会疯掉 . 后来姨妈疯掉了 . 我于是盼望着这一代疯掉的人是我 , 盼望着祖先早日把我带入那种旁若无人的境界 . 摆托这现实生活的压力与残酷 . 现在我想, 我该找这个世界谈谈那些关于我的过去 . 每个早上. 我总是醒着比以往早 . 于是获得一段独处的时间 . 我可以听自己喜欢的 the cure 乐队 . 只要声音不太大 . 坐在马桶上可以把最近一周关于 the cure 乐队的八卦新闻的娱乐报看一遍 . 剩下的时间 . 还足够一个人去一次附近的超市 . 路经邮局和一个小公园 . 在街道上我走着很慢很慢 . 像个迟缓的老人 . 仿佛已在这座城市住了几十年 . 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厌倦 . 它们也厌倦了我 . 当然 . 踩滑板 的男孩围着我飞奔而过 . 曾今攻击过我的那只斗牛犬 . 看着我从眼前走过去 . 叫都懒得叫一声 . 报摊上得阿姨在递给我报纸时 . 没有像对其他顾客那样 . 问一声早安 . 人人都再谈论着今天的雾气很大 . 而我却没有察觉到半点异常于往日 . 面对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异常, 我想我该找这个世界谈谈 . 因为我和这个世界不熟, 所以注定我该找这个世界谈谈 , 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辞藻 , 也无需过于在意自己的渺小与脆弱 . 我只是想找这个世界谈谈 . 赎回我童稚的心 , 带着应有的天真一遍一遍的默念着 , 遗忘过去 , 珍惜现在 , 展望未来 , 开始我诗意般的生活 . (完 ) <迫不得已才写这篇文章 , 因为策划早已写好了 , 题目都预定好了 . 我别无选择 . 所以我不得不在午夜绞尽脑筋虚构故事 . 当然还有的故事是以前的文章里的 , 现在重新插入新篇章 , 只要符合主题就是好故事 .> 2011年 12 月
建议你去找泰戈尔的散文
朱自清;《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