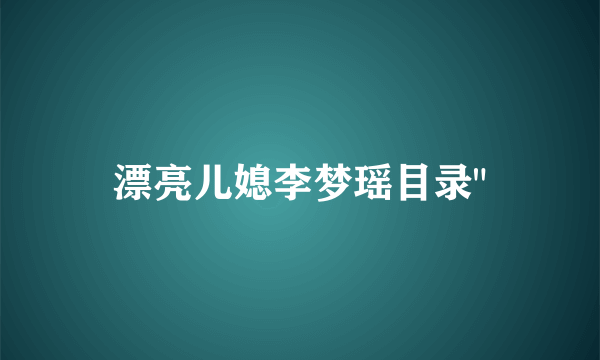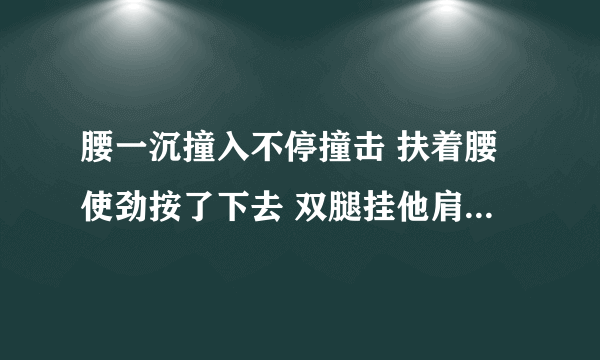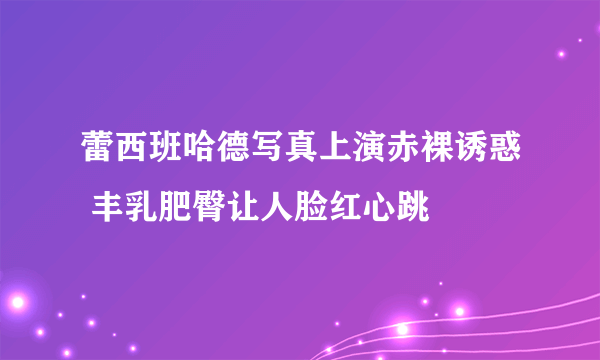(一)初遇
初六日,惊蛰,春雨不绝。
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她。
其实出发前就隐约觉得这次下山会不同寻常,因此选了这条最僻静的路,我预感会在这条路上碰到她。
我想会会这个女子。
哪怕碰到的是冤孽,我也与其躲避,宁愿交锋。这是我向来的性格。
消除恐惧最好的方法是面对恐惧。等到你离它近得可以感觉它的呼吸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你并不恐惧了。
恐惧并非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内心。
魔由心生。
和师父第一次打的机锋就是这句话。
当时他在教导我们弟子静心坐禅,入空境,断妄念。
我没有坐禅。我睡觉。呼噜打得很响。
师父很生气地用禅杖把我敲醒,质问我为什么不苦修,绝妄想。我回答说魔由心生。
师父愣了半晌,然后拖着禅杖低头走了。
断绝妄念本身就是一种执着一种妄念,你动了要断绝的心思,就是入了魔境。其实念头生生不绝,仿佛海里的浪花一样,你如何能断绝得尽?即便你自己觉得已经了断干净了,那只不过把海水排空而已,空守着枯干的海底,又有何意义?禅不是让你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而是让你得大自在。
当天深夜,师父把我叫进禅房,就是要听我说这番话的。
我说得沉稳有力。
师父又微笑着问,那你如何修行?
就让那些念头自己生灭好了,我淡淡地说,它们不过是浪花泡沫,转瞬即逝,而且没完没了。只要明白自己的心在哪里就可以了。那些泡沫迷惑不了我。
说完,我停了停,看了看窗外。这个深夜天气很好,月色的清辉洒进来,照得我雪白的僧衣一尘不染,有风微微吹过,宽大的袖口便轻轻抖动。望着窗外黛色天空的疏星朗月,我有些出神地喃喃自语:
真是风月无边哪。
然后我转过脸,目光灼灼地看着师父,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含笑不语: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听见我这句话,他专注地凝视我良久,然后长长叹息一声,轻轻说:
“你不是我佛门的千古圣人,就是千古罪人……从今后,你叫佛果吧……我有些倦了,都早些休息罢……”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仿佛疲倦得就要睡过去了。
第二天,我升为首座。
从此,我是师父最器重的弟子。
这是我第一次下山修行,师父有些担心,一直送我和师弟佛莽到山门:
“这次下山要小心啊,不要误踏了俗尘中的杂草。”
师弟支支吾吾,我知道他并没有听懂。
我看了看雨中漫山遍野枯草中星星点点的绿色,觉得早春的生机竟然是如此盎然,于是淡淡地笑了:
“师父,出门便是草。”
春雨很细很柔,落在青色的箬笠和蓑衣上,绵软得如同女子的手,很舒服。转过山坳,就看见她站在路上。前面,有条因为雨水才出来的小河,不深,但是很急。
她穿着淡绿色的衫,在雾气氤氲的山中显得极其干净清爽。油布伞下她的身影袅娜娉婷。我从来没有特意去留心看女子的背影,但也从未特意避免去看。在我看来,美丽,就是一种禅意。
我已经站在这条路上很久了——特意选择了一条被溪水阻住的山路。我在等他到来。知道自己淡绿色的衫和嫩黄的油布伞在这样春雨迷濛的山谷中干净得鲜艳。这身衣裳是我精心挑选的,低眉看了看脚上的丝履,还是雪白,没有被泥泞所污。这正是我需要的——良人,我要最完美地出现在你的视野。
我的身影修长,在伞下更显得玲珑有致。所以我没有回头看他。
我走到她的身边:
“姑娘,过不去了吗?”
我从伞下转过头,有些害羞有些焦急地望了他一眼,他在微笑,眼神清澈:
“是呀,没想到山涧阻断了路,有急事要过去呢。”我的声音怯生生的,很为难的样子。
我想了想,该来的就来罢,不管你是佛是魔,是孽是缘,我的心已经不被蒙蔽,任你斑斓绚烂,我自然光亮通透。
“这样罢,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我抱你过去。”
她看着我的目光深不可测。我从未见过如此黝黑明亮的眸子。她没有过分轻慢的举止,甚至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处子一般,却周身无处不妖娆。我终于明白,女子的妖艳不是来自面容,也不仅来自举止,而是眼神。有多少灵气在双眸中凝聚,她就有多少娇媚。
我抱起她,轻盈得恍若没有重量。她的呼吸如山谷里的野兰花,清幽地散发着香气,在我的面颊附近飘忽。我走得很慢,一方面是小心湍急的溪水,另一方面也想多享受会儿这种美丽。溪水很冰凉,从腿脚的皮肤丝丝渗进来,让我有清澈的感觉,然后就想到她刚才的眼神。我一边细细体察这种精致的氛围,一边远远地笑着对自己说:佛果,这么美好的事情既然来了,就尽情欣赏罢,不过,不要留恋啊,过去了就过去了。
我对自己笑笑,脚下沉着安稳。
她轻轻攀着我的肩膀,面容和我很近,但是我心中没有丝毫绻绮的念头。我知道,她的面容虽然清秀,但目光里没有了刚才无比旖旎的春色,既不妖媚,也不羞怯,甚至连清秀都没有了,只剩一个空字。这使我心内平静澄澈,没有一丝杂念。忽然想到佛相庄严,并不是大殿之内垂目敛眉正襟危坐的才是,这样春色温柔风月如霁何尝又不是呢。
山水盈盈中,我抱着一尊佛。
我在他的怀里,还是那么温暖宽阔的胸膛。我轻轻地调匀自己的呼吸,让自己心沉如水。他有一颗骄傲敏锐的心,却通透得无法蒙蔽。他甚至聪明得能了解自己。要诱惑一个聪明自信的男子,首先就是不能让他瞧不起你。良人,你有佛心,我有魔心。你能看出它们的分别么?如果我能让自己看不出,你也一定看不出。
很早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个道理,要让别人动心,首先要让自己动心。
我不会在这个时候就诱惑你的。
我知道,要收服你的心,必须先收服你的自信与智慧。
我要让你堕落得心安理得。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诱惑。
佛莽一直目瞪口呆地跟着,他始终搞不懂我这个师兄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反常的事情来,却不敢问,恐怕里面有什么他所不能了解的深意。他参悟得太辛苦了,以至于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其实万物舒展自然,哪来那么多深意?要走即走,要停即停,思虑那么多不是作茧自缚么?可我不能说,我一说便是我错了。只有他自己参悟来的,才是他自己的。
过了冰凉的溪水,我把她放下,合十稽首,微笑告别。我要接着赶路,前面的路还很长,出门就是草,这才是第一根呢。
师弟亦步亦趋,满腹心事地看着我,不说话。我也沉默,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你说了反而让他不能领悟,那是害了他。
终于,佛莽忍不住了:
“师兄,我们出家人的规矩,不是应该不近女色的么?”
“是啊。”
“那你刚才抱着那个年轻的女子……”他迟疑地问。
“我已经放下了,你还没放下么?”我微笑着回答。
这个细雨的春日,山岚氤氲妖娆。
(二)剃度
初九,晴。日暖风轻。
自从五年前那次下山回来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过禅寺。
因为在那次云游的路上,我在同安寺破了慧南禅师闻名天下的黄龙三关,很快声震丛林。
我想,我不必再去寻访名师了。
回来以后,我和过去完全不同,每天都坐禅静修很长时间。但是我从不在禅房里枯坐,而是在树下。
桃花树。
坐在桃花树下,我敛眉垂目,任凭缤纷而落的桃花洒满了雪白的僧衣。这个季节阳光总是很柔媚的样子,照在身上是暖洋洋的感觉。
这些年来,我的身上已经落过五次粉红娇艳的桃花。它们甚至在我雪白的僧衣上留下了浅浅的粉色的印痕,极淡极淡地妖娆着。
我依然每天都去坐禅,远离人群,独自一人。
因为我知道自己并未参透。
每次,我都能透得一切法空,但是空虽空了,却隐隐觉得总有一件事未了。它的影子非常模糊,转瞬不见,但是我知道它还在我心里。
我现在无法抓住它,这让我甚至有些恐惧。
桃花是没有馥郁香气的,但是我能闻见从花瓣和萼中散发出来的植物的清香,这种幽香使我安宁。我坐在树下,呼吸平稳。
但是我知道在丹田里那个灰影仿佛一根飘忽的针,捉摸不定中锐利异常。无论刺在哪里,肯定都会很疼。
这五年来,我一直很专心地修行,希望能够找到并拔出这根针。
师父在唤我。
今天有人归入佛门。剃度是一项很隆重的事情,我当然要参加。
我只是觉得奇怪,师父一向收徒谨慎,必须考察很久,甚至长达数年,怎么这次这么快就收下了?
我甚至没见过那人。
在我记忆中,只有我是第一次见师父就被首肯做弟子的,那是因为我是上上根器的人。这是师父亲口的话。
看来,这个人一定也有很灵透的慧根。
我没想到是个女子。
她跪在那里,衣裳洁白如雪,阳光下让人不敢逼视。她的头发很长很黑,笔直地从低垂的头上一直坠到地面,光滑如同瀑布。
师父的剃刀轻轻划过,一缕缕的青丝便无声地飘落下来。
我突然想起了落在我肩上的桃花,它们一样零落得温柔。
她抬起头的时候我立刻认出了她。
她面色苍白,几乎不见血色,更显得双眸幽深。即便没有长发飞扬,她依然妖媚不可名状,眼波流转之处,我能听见师弟们窃窃的低语声,然后在她明艳不敢直视的目光中纷纷低下头来。
他们都很年轻。
师父恍若未觉,一字一句地跟她讲说佛门的清规,声音遥远,面无表情。
我觉得丹田中的那根针轻轻地扎了我一下。一种尖锐的疼痛。
师父的话很陌生地传来:“你既皈依我佛,就应了断红尘中的俗念,世间再无秦幻真这人,从此你就叫佛萼罢。”
我等了五年才来,就是不想让你提防。
你肯定能认出我的,因为我的样子不会再变。洪荒以来,我就永不衰老了。五年前那场缠绵的春雨中,我吹气如兰,你心无旁骛,甚至在我纤细的手臂从你肩膀上滑下时你依然没有心动。知道么,在你抱我在温暖的怀时我看穿了你的胸口,看见了你的五蕴皆空,良人。难怪摩诃迦叶尊者在灵山就赞叹你根器锋利通透。我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除了偷偷衔下自己的一根青丝,顺着呼吸悄悄送入你的心内。我看见它纤长柔韧,顺着你的气息幽灵般游走,从容纠缠。
当时,你没有发觉我诡异的笑容。
头顶凉飕飕的,我满头的长发散落一地,抛却了三千烦恼丝,惟留一根来系住你的心。方丈大师的声音如遥远的禅钟飘入我的耳膜,以后你不会再叫我真真了。佛萼,这就是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面色白皙,双眼冷漠。那些在我身上畏缩着游走、不敢稍做停留的胆怯目光,只能让我蔑视。里面的欲望肤浅苍白。良人,你的目光呢?你在看我,但是眼神已经穿越了我,空寂广漠。
但我看见那如针的发丝细细而锐利的刺痛,就在你心里。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原来她叫秦幻真。不过这没有意义。从今后,她就是我的师妹了,佛萼。唔,佛萼,一个别致的法名。
初九真是个反常的春日,居然没有下雨,我想。今天有很好的阳光。
(三)机锋
佛萼的来临使得如一潭古水般的禅寺投入了颗石子。听佛莽说,有不少同门师弟很是为佛萼神魂颠倒,甚至经都没有心念了,整天惦记着找借口路过她独居的禅房,或者与她没事搭话。据说好象有几个特别狂热的甚至偷偷给她写了情书,要求私下的约会。听了这些,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滑稽得很,同时不明白为什么师父会这么痛快地收下这个女弟子。难道预料不到这些流言蜚语?
听佛莽说师父开始是不愿收的,推说她是女的难入空门。佛萼应声反驳道:“难道佛性也分男女吗?”师父语塞,又惊讶于她的灵慧,便答应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淡淡一笑。每天还是独自去树下坐禅,但是落在僧衣上的桃花日渐稀少——春天就要过去了。
十四,有风,天气微凉。
今天师父要开堂说法,早早就起身。
我到达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站得整齐,恭敬地站在佛堂前。师父也穿戴齐整,从方丈中走出。大家屏神静气,等待师父为数不多的几次开堂讲法。
我站在人群的最后一排,忽然发觉佛萼没来。
正在这时候,我看见佛萼朝这里走来。人群里立刻有窃窃的私语,那些排列整齐的光头也有些紊乱,仿佛无形中被惊扰了似的。我猜他们大概在揣测佛萼会站到谁的旁边。
她却径直向前,走到大伙的面前,转过身,面朝我们。
师父走上了佛堂,但没有说话,静静地看着佛萼的举止,没有阻拦的意思。
佛萼面对我们,朝阳洒在她的脸上身上,灿烂明艳。她目光直视我们,微微一笑,朗声说道:
“收到一些同门的信,说是对我倾慕得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既然这样,那你就现在站出来拥抱我一下嘛!”
人群里鸦雀无声。她站在我们面前,伸开双臂,胸膛挺拔,身段妖娆。灰色的僧衣在风中猎猎作响。突然觉得她其实是傲然挺立于旷野,四周空无一人。我凝望着她,有些出神。在剃度后,佛萼只穿灰色的僧衣,一种黯淡萧索的颜色。今天却发现这种萧索使得站在面前的她更显得妖艳。如果有一种妩媚能从暗淡中来,现在就是了。
师父在讲堂上突然抚掌大笑,一边笑着一边说:“如是。如是。”
然后,转身下堂去了。
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谁对佛萼心存绮念。
廿九,晴,天高云淡。
春天到秋天总是过得很快。佛萼自从那次在讲堂前要求公开示爱以后,同门都对她敬畏不已。一切流言蜚语都立刻消失了,禅寺重归平静。师父的反应已经告诉我们她其实是有多么通透的禅心。我不禁暗自佩服师父的眼光。
我依然还是每天到树下打坐,现在满我雪白僧衣的是枯黄的落叶,而不是娇艳的桃花。它们都是飘飞的红尘,无论是花还是叶。它们在我的身边随风而来,然后又随风而去。而我,依然端坐在这里。
我不愿象它们一样任意被外力摆布,永远沉溺在迷茫中。
起风了,落叶漫天飞舞,从我身边离去,没有留下任何到来的痕迹。它们的离去是多么轻易啊,虽然它们的到来也是如此的温柔。我把握不住它们,尽管那是一种绝然的美丽,我却不能留恋,只能保持自己寂然不动的心。
那么,胸口那一缕若有若无的疼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依然没有抓住那根灰影模糊的针——它不仅尖锐,还很柔韧,让我想起了……对,让我想起了那个娇媚春日里,在师父剃刀下缓缓飘落的青丝。
一根长长的青丝。
我长长地呼吸,静心听空旷树林里的天籁——这让我心空无一物,只要再透明一些,那根锐利柔软的灰色阴影就会无所遁形。
忽然,听见一阵豪爽嘹亮的笑声。这种笑声里面没有羁绊,没有恐惧,只有欢喜和自信。
我辨认出这是佛莽的声音。
心中跟着喜悦起来,看来佛莽猛然有所得了。
睁开眼,就看见佛莽昂首阔步走来,脸上满是笑容。
“师弟,刚才是你的笑声?”
“是,师哥。”
“为什么发笑?”我微笑着问他。
“刚刚站在山坡上,向前望去,看见天空高渺不可及,群山起伏到极远处,满山秋枫如血,突然发觉天地如此壮阔,我自己一点患得患失的苦苦执着渺小可笑,顿时心有所感,只觉满心自由,情不自禁大声笑了出来。”
我暗自点头,这个佛莽,看起来好象性子粗豪,心思鲁钝,但是电光石火之间本心显露。自己虽然师父一向器重,被认为慧根深厚,却迟迟透不过心内那层若有若无的禅关……佛果,你还得苦参哪。
正在思忖的时候,一个灰影从山下娉婷走来。佛萼脸上笑盈盈的,说不出的娇媚,这是一种因为内心真正的快乐而来的娇媚,纯净没有渣滓。她在我们面前站定,依然微笑着说:
“佛莽师哥,刚才我听见你的笑声了呢。你这一笑恐怕要声震三十里啊。”
她的声音婉转清脆,说不出的好听。
佛莽自从上次见识到佛萼的厉害后,一直对她敬畏有加,听她这么说,憨厚地呵呵笑了起来。
佛萼语锋一转,突然问:
“佛莽,什么是佛祖西来意?”
佛莽闻言,立刻大喝一声,震耳欲聋。他周身似乎散发出无形的罡气,一阵狂风吹来,满地堆积的落叶猛然惊起,纷纷扬扬地被吹远了。
我不禁赞叹:佛莽这一喝神似当年的义玄禅师,如坐地狮子吼,把那些执着于思忖祖师西来意的知见统统喝断。佛萼虽然公认灵性聪慧,但这次恐怕是输了。
佛萼却没有被他的猛然大喝所吓倒,依然笑吟吟地,甚至对我们扬了扬眉,眨了眨眼,秋波流转,神态妩媚之极。
佛莽愣住了。
我心里突然一闪,顿时省悟,不禁微笑着,对佛莽说:
“师弟,这次机锋你输了。”
佛萼盈盈一笑间,用绝美柔媚的扬眉瞬目破了佛莽的金刚喝,我看着,突然心里透亮,顿时明白世间万有莫不是佛法,无论是威猛庄严亦或妖冶明艳。忽然想起多年以前我抱着她过河时风月如霁的感觉。这么些年来,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去回想这个情景,不要去想她在安静如处子之中蕴藏的万种妖娆,这何尝不是一种畏惧,一种烦恼?是的,那些欲念来来去去,如海中的泡沫,如露如电,而我一直没有接近,只是远远地逃避,不断提醒自己那是虚幻。我知道自己是因为心底深处的害怕,害怕自己迷惑不能自拔。原来这么些年来,我一直没有解脱过,因为我没有沉溺过。
如果不从海里经过,你又怎知那些泡沫不会迷惑你,而你可以不被它们迷惑?
自己如此钟爱在树下坐禅,何尝不是因为桃花零落和枯叶纷飞时那种妖媚温柔的美丽?一直极力在寻找心里那最后一丝烦恼,想彻底空了自己的心,这何尝不是一种执着一种妄念一种魔界?原来烦恼即菩提,不从烦恼中经过怎么能到达菩提的彼岸?
这么想着,五年来心中的不安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转过脸,微笑着看佛萼,淡淡地问她:
“佛萼,是入佛界难,还是入魔界难?”
她也笑了,悠悠地回答:
“恐怕还是入魔界难,入佛界容易多了。”
“哦?可是我们出家人修行,就是为了入佛界啊,有多少先辈大德修了一辈子都修不到,这还容易?相反,多少俗世凡人轻易就入了魔界,无法堪破啊。”
“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真正的入魔界是自知魔界而入。佛门子弟谁不是为了入佛界苦心修炼,对魔界却惟恐避之不及?虽说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皆有法身,可是又有几人能够诚实地面对天地万象呢?至道无难,惟嫌拣择。”
我不再说话,心中愉悦地看着她。
她也在注视着我,眸子漆黑,和当年一样深不可测。她灰色的僧袍上是树影的班驳,有风吹过,宽大的衣袖便轻盈地飘动,显出身段完美的轮廓来。她就站在我前面,漫天飞扬的落叶中,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楚楚动人。我看着她苍白的(um是什么单位?um是一个长度单位,它表示的意思就是微米。长度单位除了微米外,常见的还有cm厘米,dm分米,m米以及km千米。1mm(毫米)=1000um(微米),1um=1000nm(纳米)。)脸上慢慢展现一个笑容,一个只给我的微笑,里面的含义只有我们知道。这个笑容妖娆,绝美,但是又很从容,仿佛她手上正拈着一朵莲花。
我静静地看着她,这次,我知道自己没有逃避到远处,而是全身心地凝视着她。
她看得懂我的眼神。
是的,我看得懂你的眼神。这么久了,我一直在等你这个眼神,良人。
我久久地注视坐在树下的你,看着你的笑容亲切,神情洞察。千年以来,你的这个样子一直如此让我眷恋,了然自信的目光中散发着不可抑制的漫不经心和随心所欲,好象在告诉我你的平和温柔完全是来自你的满不在乎。万物都是禅意都是佛法,也都是空。你的心凌驾于一切之上。
可我就是要你注视我,在意我。我要让你离不开我。我要让你堕落。
但是我知道你的智慧。
可我也有智慧,我知道如何收服你。
我要真正地诱惑你。
还记得我对自己发过的誓言么:我要让你堕落得心安理得。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诱惑。
我是妖娆的化身,不要忘记这点。我用妖娆破去了佛莽的金刚喝,也要用妖娆战胜你的智慧。其实,妖娆何尝不是一种智慧?谁能象我这样临风而立,不举手,不投足,眼波流转,尽得风月?
是的,良人,我要让你不迷惑,心甘情愿地沉溺。谁能说清这是昧还是不昧?
我不管。
我只要诱惑你。
秋天的景色总是很美的,尤其是今天,廿九,秋风萧瑟。我和佛萼一起看满山的秋色,一直到天色暗淡。
(四)绻绮
三十,夜,多云,有大风。
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夜已经深了,**着墙壁,沉沉睡去。
自从在树下打坐以来,我似乎喜欢并且习惯斜倚着休息。
秦幻真出现在我面前。
她依然是满头黑发如瀑,定定地看着我,然后慢慢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触碰我的脸。
为什么我会记得她是秦幻真?
她应该是佛萼啊。
但是我一点都没有惊异。
“真真……”我喃喃地叫着。
窗户忽然洞开,秋风吹过,长长的黑发立刻飞舞起来,遮住了她白皙的脸庞,闪亮的眸子在黑发后面若隐若现。
我怔怔地看着,那是一种让人心碎的凌乱的妩媚。
在这样一个暗夜里。
我满身大汗,猛然醒来。
四周是一片寂静的黑夜。
秋风在身边呜呜地吹着,仿佛天幻箫音。
然后我就看见那个灰色的影子飘到我面前,风姿绰约。
我看见她美丽的眼神,专注而绝望。
长长的睫毛下,眸子在没有光的黑夜里如星星一般闪着微光,诱惑我的灵魂。
是的,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深情妖娆的目光,仿佛是无数旖旎的青丝,将我捆绑起来。
“佛果……”她象风一样飘进我的怀里,双臂缠绕上我的脖颈,宽大的袖子滑落,我可以看见她的手臂纤细苍白。
她低低唤我的名,如同叹息一般,我可以感觉她的身体贴过来,玲珑有致。
她的唇湿润柔软,轻轻贴上我灼热的双唇,这种沉醉般的妖娆让我心中迷茫一片。
我情不自禁闭上眼睛,心中喃喃地问自己:
不思善,不思恶,这颗本心该如何?
既然要沉溺,就让我痛快地沉溺罢。
我一把揽住她的腰,那里纤细而柔软。
她轻轻解开带子,宽大的僧衣便在秋夜里随风飞舞,露出洁白完美的胴体。
我手臂一用力,她的身体就紧紧地靠了过来,肌肤光滑,起伏圆润。
我听见了她的呼吸。
如水一样的呼吸,慢慢淹没我。
我看见绵绵春雨中的自己抱着她。
她吹气如兰,在我的脸颊略过。
脚下溪水冰凉。
淹没就淹没罢,我对自己说。
寒冷的秋风中,我们的身体滚烫。
而她的僧衣猎猎作响。
我紧紧地贴在你的胸口,良人。
那片宽厚和温暖是我千年以来的梦寐以求。
为什么不肯睁开眼睛?
多想看看你的眸子,看看你是否会象我这样纯粹绝望地凝视你。
你离我有多近呢……
然后我就感到暴风雨的来临,而我象狂暴的大海中飘摇的一只小舟。
除了死死地抱住你的脖颈,我什么也不能做。
我已经被你震去所有的知见和执着。
什么主宾,什么人境,统统都没有了,在你的暴风雨中,只有空。
甚至连空也没有了。
第一次进入这种境界。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界,佛界?
魔界?
可我知道这是让我无尽欢喜的境界。
我听见你在唤我的名字,“真真”,是的,你在叫我“真真”,而不是佛萼。
喜欢听你这么叫我。
我快要沉溺了,良人,这种沉溺让我迷恋不舍。
终于明白,要你沉溺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沉溺。
我愿意。
良人,我要和你一起沉溺在这种境界中,管他是佛界是魔界。
别离开我。
可是当风雨平息后该如何呢?
你过了魔界后会如何呢?
你还会在乎我吗还会眷恋我吗?
我忽然有了大恐惧。
这种恐惧让我在你的风雨中战栗不安。
良人,我很害怕。
我能感觉到我们的身体湿淋淋的。
是的,本来我们就在被淹没。
可是现在我感觉自己的眼眶里也湿淋淋的。
我在流泪,良人,因为大恐惧而流泪。
我知道你要离开。
我不知道。
我不敢知道。
我死死地抱住你,可我还是很害怕。
你会离开我吗?
良人,我不敢问。
因为我不敢承担。
终于知道如何留住你,别忘记我的智慧。
我要永远的留在魔界里,也要让你永远地留在魔界里。
这样我们就不会分开了吧?
是不是?
我逃离不了这个大海,也不要让你逃离这个大海。
这是我的智慧。
我决定了。
我死死地抱着你,把脸藏在你身后。
在你身后,我泪如泉涌。
然后我咬着自己的长发,在你的耳畔悄悄地笑着说了一些话。
其实我也没说什么,就是告诉了你我的来历和我这么些年来处心积虑要做的事情。
最后说,我做到了。
不知过了多久。
我一直没有睁开眼,直到她在我耳边盈盈地说出那些话。
很奇怪,佛萼说完我居然很平静,甚至没有愤怒。
我称呼她佛萼就说明我已经很平静了。
至少我必须平静。
佛萼其实并没有欺骗我,一切都是佛法。
她的智慧是,她的妖娆也是。
我本来就是为了到魔界的。
我到了。
而且没有被溺毙。
现在我要穿越魔界,对岸就是佛界。
临济义玄大师曾经说过:
遇佛杀佛,遇祖杀祖。
既然过去了,就过去了。
不要留恋。
我懂得大师的意思,知道该怎么做。
三十,夜,大风,暴雨忽至。
我大喝一声,拿起禅席下的戒尺,用尽全力打在佛萼头上。
脑浆和鲜血溅满我赤裸的身体。
没有星光的暗夜里,可以听见我的一句轻诵:
“阿弥陀佛”。
(五)佛裂
初一,凌晨,有大风,雨未停。
我身着雪白的僧衣,慢慢走向大殿。脚步沉稳。
一路上,不断回忆着小时候自己在岸边玩沙子,把它们捏成小小的佛像,可是水分一干,佛像就会裂开。
我拼命捏啊捏啊,一边哭一边捏。
我不要裂开。
可是我感觉自己在裂开,碎片不断地掉进大海里。
我不知道对岸还有多远,也许在到达以前自己已经完全破碎掉了。
统统沉入魔界。
我在拼命捏,一边捏一边爱着恨着悲伤着。
佛祖啊,居然有这样的爱恨这样的悲伤这样的绝望。它们从四面八方撕扯着我。我快抵御不住了。
我的眼眶干涸,脚步沉静。
我迈进了大殿,趺坐在佛像前。
我要离开这里。
阴森的大殿中,我沉默地端坐在佛像前,僧衣洁白如雪。
里面是我布满佛萼的鲜血和脑浆的肉身,很肮脏。
超脱这个肮脏的魔界,超脱欲念的撕扯。
超脱爱恨。
让我选择遗忘。
这是我肉身最后的意识。
在黎明前的黑暗过去的一刹那,我脱离了躯体。
我终于到了佛界。我想。
我在大殿之中漂浮,俯瞰宽广的大殿,在檀香中袅绕,想纵声大笑同时放声大哭。
佛祖,这是我的智慧和信心吗?这是我的根器锋利吗?
冥冥中,绝望的悲伤让我极度亢奋,觉得浑身充满力量。
没有什么我不能战胜。
我穿越了魔界,又亲手毁灭了魔界。
我是佛。
初一,阴,早晨风雨不歇。
佛莽第一个上堂,发现佛果趺坐在佛像前,大惊。
他在殿里大叫:“佛果师兄坐化了!佛果师兄坐化了!”
方丈赶来。果然,佛果端坐在佛像前,面带微笑,苍白如纸,身躯冰冷。
这时候,佛像突然开口:
“我已成佛,你们不必惊慌。”
僧人大惊失色,转过脸看着殿中的佛像,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佛像继续微笑低眉垂首,开口:
“你们不信,可以看——风停。
雨歇。
云开。”
风停。
雨歇。
云开。
第一缕阳光照进大殿,落在我的脚下。
法力无边。
我端坐大殿中央,纵声大笑。
笑声里充满疯狂。
方丈大师突然大喝一声。
仿佛半空突然响了个炸雷,一直劈入我的心内,顿时一片迷茫,张着嘴一动不动。
他用手在空中一扯,我感觉有什么从我心里通过嘴被他扯了出去。
所有的力量全部消失。
然后发现自己的元神象风干的沙子一样涣散。
茫然地抬起眼,最后的视野中,方丈大师的手上有一根长长的青丝。
立刻明白一切。
春雨中放下秦幻真时她诡异的笑容。
在桃花树下坐禅时那个尖锐柔韧的灰影。
这根长长的头发一直深埋于我的元神内,纠缠它,也维系它。
终于明白,我一直是魔。
进入了佛身依然是魔。
那根发丝进入我的五蕴时就已注定。
可是,佛和魔又有什么分别?
!
这次,我参不透了。
太累了。
到不了岸的。
我对支离破碎的自己说。
在分崩离析前,我看见她的眼睛。
妖娆妩媚。
在大海的下面望着我。
佛萼漆黑的眸子瞬间无限扩大,将我吞没。
一片黑暗。
佛像慢慢裂开,古老的檀木发出时而清脆时而低沉的吱吱嘎嘎声音。
刺耳诡异。
宋绍兴五年十一月一日凌晨,大风雨。
成都府昭觉禅寺僧人佛果克勤在大殿坐化,佛像无故说话。后自裂。
(转笔友宇之小作一篇)